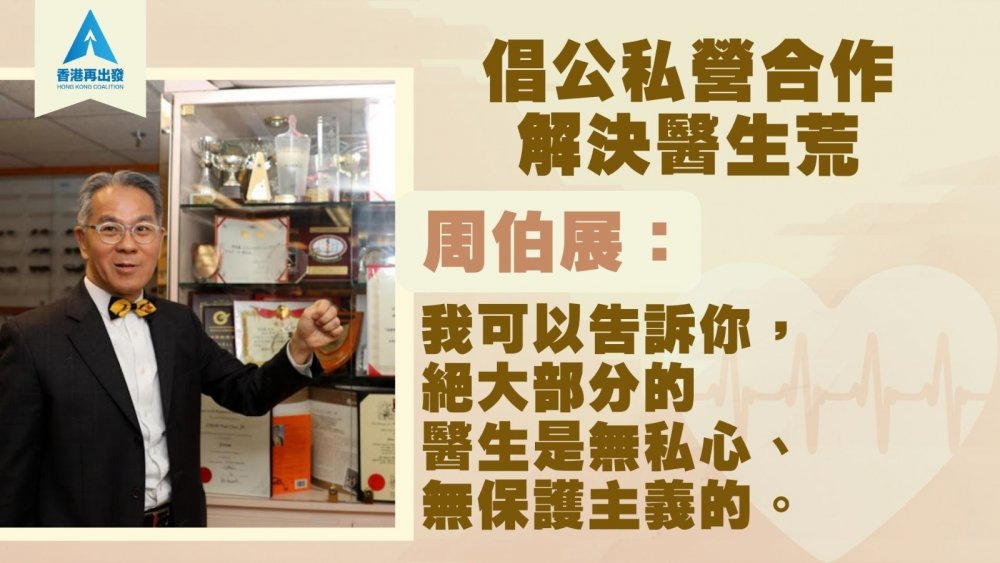
「我們醫生看問題,就好似看病。你能夠醫到病源,便能夠根治。」資深眼科醫生周伯展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,深知香港公營醫療系統超負荷,但要解決這「老大難」問題有何良方?對於政府擬允許合資格海外港人醫生免試回港執業,周伯展察覺到僅能解決部分問題;要對症下藥,他獻策政府全面推行「公私營合作」,認為有望即時解決醫生與病人比例失衡問題,「是我們做過的辦法、做着的辦法;一個行政命令,明日已經可以做到。」
香港人口約750萬,平均每1000人對兩名西醫,人均醫生比例遠低於新加坡、日本、美國、澳洲等其他先進經濟體。而在「兩條腿走路」的醫療制度下,全港大約有14000多名醫生,在公營、私營醫療系統約各佔一半,但住院病人大多只能選擇公營醫院,主因是公營費用約九成是政府津貼的。
「公營病人不肯去私營,私營醫生想去公營幫忙,公營又唔准。」本身私人執業多年的香港智庫「香江智匯」會長周伯展指出,公營醫生「做到死」,問題正正在於太過失衡,最應該做的辦法就是「公私營合作」。
「公私營合作便不需要遠水救近火等候外來醫生,更不需要由中學畢業生開始培養。」周伯展表示,這方法不需要「遠水救近火」等候外來醫生,更不需要由中學畢業生開始培養,由讀醫科、專科加上實習,共需花上13年,「你(政府)馬上落行政命令,明日我們就『公私營』喇!」
類似的公私營合作做法,本港早有先例可循。2007至2008年,當時身為香港執業眼科醫生會會長的周伯展,與醫院管理局合作展開「耀眼行動」,是第一個透過公私營合作模式增加服務量的計劃。「當時在醫管局(公立醫院)輪候的白內障病人有三萬多個,要等五年幾才排到隊做手術。」周伯展指出,「耀眼行動」推行兩年,病人等候時間縮短到兩年以下,證明公私營合作計劃可行。
除了縮短排期,若做一隻眼白內障手術,病人獲政府資助後只需自付不多於8000元,「第一贏當然是市民、病人;第二贏是我們幫了政府,政府醫生不用太辛苦;私家方面亦有未站穩陣腳的醫生,收便宜點但有病人讓他做,是三贏甚至四贏。」
至於現時政府提出引入「外來醫生」方案,周伯展認為僅能解決小部分問題,原因不是醫生多反對,「我可以告訴你,絕大部分的醫生是無私心、無保護主義的。」醫生都是以病人健康為先,自然會關注如何確保「外來醫生」的能力達標。
「醫生都是以病人健康為先,自然會關注如何確保「外來醫生」能力達標。」
不過,更令周伯展擔心的是有多少港人子弟醫生願意回港?例如本港醫院現時的工作環境可能嚇怕不少海外醫生,「你知不知道,一個眼科專科醫生,一朝早看門診要看幾多人?是60個!就算由九時做到下午一時半,差不多五分鐘不夠就要看完一個(病人),幾乎完全沒有眼對眼的交流,怎會有空做呢?」
「所以只用(修訂)法例去幫助解決醫療的問題,是不足夠的。」周伯展認為,最能快捷幫助緩解「公營醫生荒」問題,答案就是公私營合作,「明日就搞掂喇」,引入境外醫生需時更久。但放眼將來,要解決醫療體系上的問題,本港是否有行之有效的答案?周伯展說,除了人手不足問題,其實護士、物理治療師,甚至是醫院、手術室、病床、儀器等等,全部都不足夠,「長遠來計,還是要看當政者的長遠眼光」。
「一啲都唔痛。」周伯展早於今年三月已在私家診所接種了科興疫苗,接種後沒有感到身體不適。目前本港新冠肺炎疫情緩和,周伯展覺得只是幸運,未敢樂觀,認為世界各地疫情仍然嚴峻,「疫情不單止未過,還恐防會再大爆發,最壞的可能都未來到,所以大家真的不可以放鬆」。
為了有效防疫,周伯展認為政府應效法內地,做好「外防輸入,內防擴散」,當中內防擴散要早發現、早隔離、早醫治,建議盡快安排做一次全民檢測,找出所有隱形傳播者。
個人防疫方面,周伯展呼籲市民要盡快接種疫苗,並提醒市民:「要記住,疫苗是我們抗疫的一種手段,而非所有的手段,並非打了針便了事。因為這種病毒很『蠱惑』,時常會變種。」
除了接種疫苗,周伯展說,市民仍要繼續戴口罩、勤洗手、不要亂摸臉,盡量不要去人多擠擁的地方,要緊記「這場疫情未過去的,我們還未打贏仗的」。
為什麼有病人的眼睛無毛病但目光遲緩?為什麼有病人視力復原但仍然不開心?行醫超過30年的周伯展說:「我們不要只做『器官醫生』,而是要『全人醫治』,不只要看病人的身體,還要看他的精神和社交,不是只醫好你隻眼。」
周伯展有一名病人是海員,退休後由女兒陪同往求診。周伯展見到這名海員時,對方神情呆呆滯滯、目光遲緩,不眨眼、不答話,檢查其眼睛卻沒發現結構上的問題。周伯展追問下,始知這名海員在航海回家前,在船上的歡送會與船員賭錢,把身家都輸光了,然後他整個人一直呆滯,「如果是好忙的診所,可能檢查後會說無問題;但我們追問下去,才知他不只要看眼科,更加有需要向精神科求醫」。
另有一名中年女病人,年幼時其中一隻眼不幸損壞了,眼球萎縮,眼窩凹陷。後來,她另一隻眼也不幸患上白內障、青光眼等眼疾,連視網膜也脫落了。周伯展盡力為她醫治,但她的視力復原後,仍然表現得不大開心。
追問之下,周伯展才了解到,原來病人因為另一隻眼自幼萎縮,只剩眼眶,令她一向十分自卑。周伯展於是為她安排裝上義眼,病人重拾自信,恍如重生,「雖然隻假眼是看不到東西,純粹是美觀,但對於40多歲的女士來說,她對自己(外觀)也是有要求的。我們幫她裝假眼,她整個人立刻不同了,又去唱K,又去不同社交活動」。
周伯展說,這些病例均令他深深感受到,為病人看診,不應只看對方雙眼,還要看「整個人」,才能察覺病人各方面的問題所在,對症下藥,「這才是一個醫生的工作嘛!」
小時候健康欠佳、父親晚年飽受疾病煎熬,令周伯展立志學醫幫助更多人。在上世紀70年代,他考入了香港大學醫學院,讀完五年醫科、一年實習後,面臨兩個選擇:一是掛牌做普通科醫生,一是選一門專科去學。他說,最終選擇考取眼科醫生執業資格,是因為「眼科是很奇妙的」。
在周伯展求學的年代,本港還沒有眼科的執業資格考試。他於1980年先是在香港接受眼科專業的在職培訓,1985年取得獎學金赴英深造,是本港第一批接受相關培訓的眼科醫生。學成回港後,他在公營醫療系統服務三年,至1989年在旺角開設自己的私人診所。
當初為何會選擇眼科?「我當時看到眼科的發展是會很快速騰飛的,當時的科技已看到正在趕上來,包括我們現時正在使用的超聲波、激光、微創手術,越來越多這種儀器,很振奮。」周伯展說。
對周伯展而言,另一重要原因是眼睛雖然「器官細細」,卻是人類吸收外界資訊的主要窗口。而且,眼睛是人類活着時全身唯一可看到血管的器官,若檢查眼睛時察覺眼底血管異常,有助發現病人患了什麼病,例如血管收窄,可能是血壓高、糖尿病及血管發炎等問題所致。他認為眼睛是人體最奇妙的器官,「是非常乾淨,容不下一粒沙子,是最重要的器官,是靈魂之窗」。




